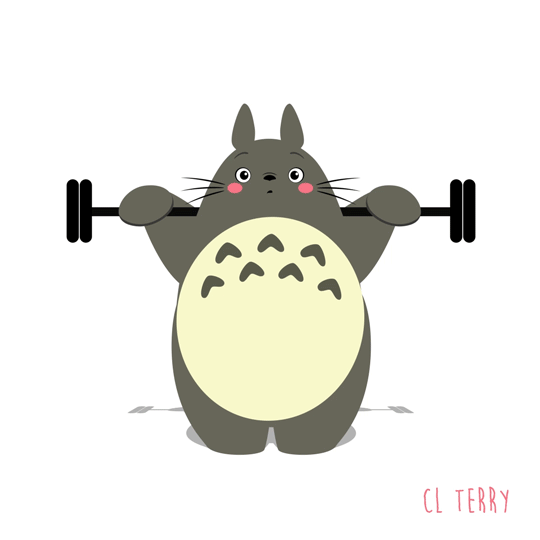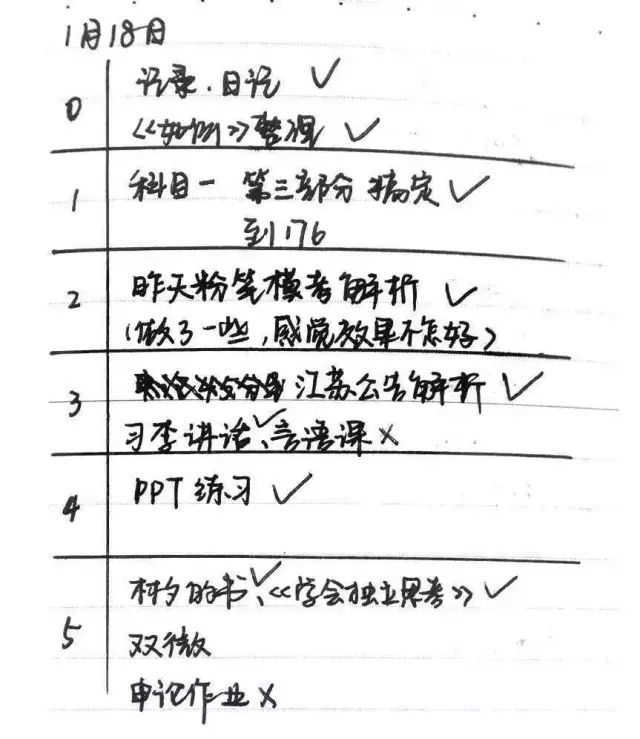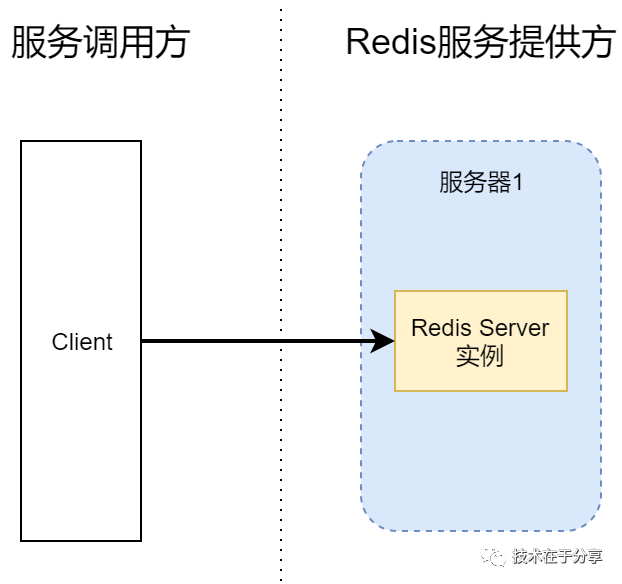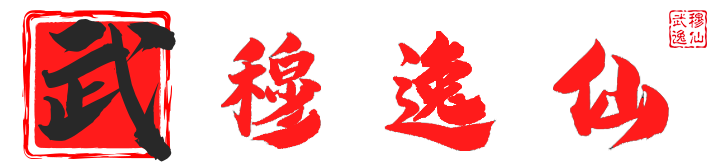黑夜一眼望不到边,给人一种强烈的窒息感。从奇山陵园回来的邱岩,睁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陈江河见了,满脸忧虑地问妻子:“邱岩怎么了?”
骆玉珠说:“发烧,连着几天了,没怎么吃饭,哭不出声音来,医生分析这种低烧是心理影响身体,让我们想办法诱导她发泄出来。”
另一侧的屋里,王旭正扒着窗户偷偷听着。
陈江河压低声音:“要让她哭出来!从小至今,孩子跟她爸相依为命,支柱突然倒了,她一下子接受不了。”骆玉珠点点头,无声地叹息说:“她妈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,再这样下去,我怕这孩子真憋出毛病来了。”
夫妻俩愁苦对坐。骆玉珠轻手轻脚推门进屋,邱岩合上眼睛假装睡着了。骆玉珠掖掖被角,走了出来。
第二天早上,骆玉珠拉着邱岩来到了稠州公园树林里漫步聊天,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,温柔的阳光照耀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,脚踩在落叶上,四周寂静无声。看着神情黯淡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邱岩,骆玉珠倒吸了一口冷气,拉过邱岩在椅子上坐下,亲切、安详地说:“来,咱俩歇会儿。邱岩,跟干妈说说,你现在是怎么想的。”
邱岩还是不吱声。骆玉珠攥着她的手:“还记得你妈妈长什么样子吗?过几天她就来了。”邱岩依然不动声色。骆玉珠摸摸她的额头,很是担忧:“现在就咱俩没有别人,邱岩,你如果难受就哭出来。”邱岩默默摇头,骆玉珠焦急了,“你可不能什么心思都藏在肚子里呀,干妈求你了!你太小了,不能什么难处都自己扛着。说出来,我跟你一起难过,一起伤心好不好?”
邱岩呆滞的目光看得骆玉珠心里发冷。骆玉珠干脆蹲在邱岩面前,诚恳地说:“干妈很小的时候妈妈也没了。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,只知道傻玩,偶尔想妈妈了就哭一阵子,总以为妈妈会回来。因为妈妈在世的时候,经常藏在电线杆后面,等我急得要哭时,她才出来,伸出双手冲我笑。”
邱岩嘴唇颤抖,骆玉珠泪水盈眶,哽咽道:“那时候可傻了,我一出去就找电线杆,找墙拐角,以为妈妈会在那里躲着……就这样过了好多天,我突然懂了,走了的人再也不可能回来了!她不会躲在后面等你回头,以后的路只能自己走……”
邱岩忍住泪水,咬住嘴唇望向别处。骆玉珠声音颤抖着说:“邱岩,将来当然会有爱你的人出现,陪你走后面的路。你也要相信,爸爸并没有走远,他没在你身后,而是在你前面望着你!你每往前走一步,他都会为你高兴。”
邱岩的泪水缓缓淌落,抽泣道:“我答应过爸爸的,要坚强,不能哭……”骆玉珠盯着这一双美丽的大眼睛,眼神中闪过一丝心痛,她用力搂住邱岩:“傻孩子!你爸爸想的是你后面的路,他是怕你受罪啊!”
邱岩“哇”的一声,倒在骆玉珠怀里号哭起来。
骆玉珠也是泪流满面,再吸一口公园里的空气,感觉舒服多了,喉咙里竟然有了甜味。
骆玉珠没有想到,邱岩不哭则已,一哭就哭个不停。从公园回到家,从上午一直哭到晚上,嗓子都已经沙哑了。骆玉珠什么办法都想了,就是劝不住!不过,邱岩退烧了。
王旭背着书包放学回来,拉开邱岩卧室的门就要进去,被骆玉珠一把拉住:“干什么去!别添乱了!”陈江河却是偷偷拽了拽骆玉珠,使了个眼色。骆玉珠放开手,眼巴巴地看着儿子进屋,坐到抽泣的邱岩身边。王旭也不说话,从包里掏出随身听连上耳机,戴到邱岩耳朵里。邱岩抽泣着,这正是爸爸去世那天听的音乐,乐曲悠扬婉转,邱岩慢慢地抽泣放缓了,最后终于停了下来,邱岩合上眼疲惫地睡去了。
二
邱岩的心态慢慢平复下来,重新到学校上课了。体育课上,邱岩跟随着王旭在跑道上奔跑。体育老师远远地喊她:“邱岩!”邱岩停住脚步,大口喘息,怔怔地望着操场的另一侧。
一位戴着墨镜的年轻女性,在老师的陪伴下款款走来,走到邱岩面前,摘下墨镜蹲下,搂住邱岩:“叫妈妈,我是你的妈妈!”邱岩神色恍惚,一动不动任由妈妈搂抱着。
收摊了,陈江河夫妻俩开车到校门口来接王旭和邱岩。王旭从校门口跑出来,却不见了邱岩身影。骆玉珠急了:“邱岩呢?”王旭闷头要上车。骆玉珠急了:“这孩子!还跟我装哑巴呢!邱岩怎么不一块儿出来?”王旭爱答不理地:“她妈妈来接她了!上课的时候就接走了!”骆玉珠吓了一跳,忙掉转头盯着陈江河。
“快,车子掉头。”骆玉珠大声叫起来。夫妻俩来到豪华的义乌大酒店,按照服务员的提示找着门牌号,陈江河按响门铃,听到屋里隐隐约约传来了邱岩的哭泣声,来开门的是一位打扮入时的大眼睛美女,非常警觉地上下打量着陈江河夫妻俩。
陈江河热情地问候:“您是嫂子吧,我们……”邱岩妈妈打断:“陈江河,陈先生?”陈江河忙笑:“对!这是我媳妇骆玉珠,快叫嫂子!”骆玉珠边打量,边强挤出笑容:“嫂子。”邱岩妈妈疲惫地侧身一让:“两位请进吧。”骆玉珠进屋,但没有看到邱岩的身影。
邱岩妈妈平静地说道:“我正想找二位呢,孩子一整天也没跟我好好说一句话,闹着要走,被我锁在里面了。”
邱岩听到陈江河夫妻的声音,拍门大叫:“我不走!我要回我干爸家!”骆玉珠心疼地皱起眉头:“你先把孩子放出来吧。”邱岩妈妈转身拿钥匙开门,邱岩从门里冲出,扑到夫妻俩身前:“干爸!干妈!”骆玉珠一把搂住孩子坐下,像分别了很久很久。邱岩妈妈难过地看着骆玉珠和邱岩。陈江河忙插话:“孩子认生,熟悉就好了。邱岩,妈妈来了还不高兴啊?”
邱岩瞥了眼妈妈,低头不语。陈江河赔着小心问候:“嫂子,听我哥聊起过,你跟邱大哥是大学同学?”
“当年他不听我的劝,非跑回这个破地方。如果跟我出国,完全是另外一种 life,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。”陈江河皱起眉头看着她。邱岩妈妈叹息说:“这个小城镇是卖假冒伪劣小商品的,在这里能有什么出息?真不知道她爸爸是怎么想的。”
骆玉珠感觉胸口被刺了一下,刚要站起来反驳,被陈江河按住。邱岩更是愤怒:“我爸爸干的是大事!这里卖的都是好东西!”邱岩妈妈瞪着女儿:“你懂什么!”邱岩理直气壮地回答:“我懂,爸爸都给我讲……”邱岩妈妈指着女儿:“Children?should?be? seen?but?not?be?heard,OK?”
骆玉珠懵懂地瞥了眼陈江河,嘴角露出不屑。邱岩妈妈强拉女儿到自己怀中:“我是要带邱岩回美国的,让她知道世界有多 splendid!”邱岩挣脱开来,来拉扯骆玉珠的手,陈江河咳嗽了一声,骆玉珠只得松开孩子。
从酒店出来,骆玉珠气不打一处来:“拽什么拽?明明是一个中国人,非说那种鸟话,在我这装洋气!我骆玉珠这辈子也不会说这种话!”陈江河叹了口气:“邱岩跟着她妈出国,恐怕很不情愿。”
“那你还让我放手?不把孩子接回来?”陈江河无奈:“那是她亲妈。”骆玉珠抱起胳膊望着窗外:“反正我想不通,邱大哥那么好的人,怎么找了这样一个女人。”陈江河叹息:“所以他们才离了。”
夜深了,洗澡后的邱岩一手用毛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,一手去拿挂着的吹风机,调试摆弄按钮时,突然一股热风随着轰鸣声喷在脸上。邱岩“啊”地一声,吹风机“咣当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外间屋里妈妈不经意地问:“怎么了,宝贝?”邱岩捂着脸:“这吹风机我不会用,烫着了。”妈妈显然没听清,心不在焉地问:“what?”邱岩走到门口,妈妈正热切地捧着电话跟话筒另一端的儿子说着:“baby,妈妈也好想你啊。接了姐姐,明天妈妈就订机票赶回来啦。”
邱岩怔怔地看着妈妈。妈妈没有察觉,压低声说:“什么?不想要姐姐?别哭别哭,妈妈没说姐姐跟咱们一起过啊,她不住在家里,妈妈保证!宝贝亲一个!”邱岩一动不动地靠在门口,妈妈一回身呆住了,挂上电话,局促不安地上前蹲下。尴尬地解释:“岩岩,你弟弟一直在哭,妈妈是在哄他……”
邱岩轻声要求:“我不跟你们一起过,你想把我送到哪?”妈妈用复杂的目光盯着女儿,轻轻地揽住她的肩膀劝道:“美国有特别好的寄宿学校,当然你愿意住家里也可以,咱们慢慢来,给妈妈点时间好吗?”
邱岩面无表情转身进屋,门“咣当”一声撞上了。妈妈身子一颤,痛苦无奈地望着女儿的房间。
三
清理三角债的会议如期在商城会议室召开了,商户代表们来得很齐,但老董等外地的代销商却没有出现。陈江河站在当初邱英杰的位置上,扫视了大家一眼:“邱大哥走前的最后一句话,还在问我欠款追回了多少。他不在了,我来替他主持这个多方协商!”眼前,每个人的面色都很凝重。
“有的人不肯来,没关系。除非他不想再跟义乌做买卖,大伙的眼睛是雪亮的,谁欠款最多、拖得最久,我们今后任何一个摊位都不会跟他做生意的。商,无信不立,这是邱大哥说给我听的,我就送给在座的每个人吧。我们要做出规矩来,那样才会有更多的人追随。如果你想挣一笔就走,你可以投机取巧,可以骗人,但你决不会长久。我相信来义乌的人都是想做长久买卖、做大买卖的!这是我拟定的章程草案……”
大家人手一份草案,热切地讨论着,陈江河边听边记。
“欠款能补多少就补多少,实在为难的,我们可以商量,但总得有个期限吧!”
“对,还可以拿货来补,尽可能把市场盘活。比方说我手里压的其他货,可以抵押……”
代销商没有出现,讨债的厂商却接踵而来了。陈江河和骆玉珠在商城摊位里各自应付着,说得口干舌燥也不顶事。
“等钱一到,这三笔款我一起打给你。我陈江河什么时候欠过别人的钱了?”
骆玉珠解释:“吴厂长你别冲动,如果我账上有一分钱,都给你打过去!可现在你让我上哪儿要钱去?”
陈江河应付着众人的讨要,突然瞥见摊后闷头坐着的夏厂长。他忙上前招呼:“老夏,你什么时候来的?”夏厂长勉强笑笑:“坐半天了。”陈江河歉疚地说:“那笔货款等我……”夏厂长起身掩饰:“没有,我就是路过来看看。走了。”夏厂长意味深长地拍拍陈江河的肩膀,转身要走。陈江河想请他吃个饭,却怎么也拉不住。“这个老夏!”陈江河望着老夏消失在小巷中。
都是要债的。一天下来,陈江河焦头烂额。开车回家也是闷着头,忧心忡忡。骆玉珠转头看他,轻轻地将手搭在他的胳膊上,想让他放松一下。骆玉珠安慰道:“别急,总会有办法的。”陈江河叹息:“死猪不怕开水烫,现在谁家不是焦头烂额的。我是心疼老夏呀,他那五金厂肯定是撑不住了才来找咱们的,可他什么都没说,反倒弄得我很难受。”
货车快到家时,远远地望见有人正在砸院门。“陈江河!骆玉珠!我知道你们在家。”王旭在院里喊:“爸妈真不在!我骗你干嘛?”陈江河脸色一变,刹住车停靠在路边,骆玉珠快步走过去。
“孩子,我跟你爸你妈是朋友,你赶紧开门让我进去吧。”王旭:“我没钥匙!我爸我妈出去了!”
骆玉珠走近才看清:“吴厂长?”吴厂长转身愣住:“骆玉珠,你们两口子也真是,躲什么啊?”骆玉珠瞪眼:“堵我们家门口要钱来啦?”陈江河快步跑来:“老吴,可真有你的!追到家里来了?”吴厂长哭丧着脸:“你俩多少给点呀,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啊。”
骆玉珠打开院门拉住儿子:“来,看家里什么能搬,你带人全搬走。”吴厂长尴尬:“你这是干什么?江河,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了,你瞧你媳妇……”
陈江河拉过骆玉珠,一边面对吴厂长:“老吴,你再容我两天。”骆玉珠不依不饶:“你又是到摊上要债,又是砸我家门,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了,你不知道我们俩的为人吗?”陈江河瞪眼:“少说两句!”陈江河拉过吴厂长低声解释:“我欠人货款最多的不是你,是五金厂的老夏。你瞧人家!”吴厂长哭丧着脸:“我来你家也是硬着头皮,我们的厂收不回资金,后面也开不了工,不是只有你们一家欠款,现在大家都赖着不还啊!”
骆玉珠问:“我们会跑吗?”吴厂长快哭出来:“你们两口子倒不会,可其他人都跑了,除了你们,我谁都联系不上啊!”陈江河与骆玉珠一脸无奈。
吴厂长走了,夫妻俩电灯也不敢开,只敢蒙在被窝里,用手电筒打光,数一数代理商打的白条。院门外又响起了敲门的声音,寂静的夜里,让人听得心惊肉跳。外间屋里王旭迷糊地提醒:“妈,又有人敲咱院门了。”骆玉珠轻声道:“睡你的。”听见屋内长久没有声音,外面恢复了宁静,陈江河这才叹了口气:“不知道这又是谁。”骆玉珠猜测:“好像是毛巾厂的。不管他,接着数,多少钱啦?”陈江河回答:“二十七万。”骆玉珠眉头紧锁:“老董家欠得最多,他一家就欠咱八万!”
陈江河不敢看书,就打开收音机,蒙在被窝里调小声音,听一会儿新闻,里面传出播音员的声音:“全国清理三角债一盘棋,需方拖欠付款超出期限二十日以上或无理拒付的,供方有权先行停止继续发货,同时以电报或传真方式,抄报需方主管部门及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……”
骆玉珠也钻进被窝专注地听着。陈江河叹息道:“不光咱们难啊,在哪都一样,国家比咱还急。邱大哥看得远,早就提醒咱留住资金,当初真该听他的!”骆玉珠说:“再不还款就上法院告去。”
“老客户能撕下这张脸吗?以后买卖还做不做了。再说就算告他赢了又怎么样,现在欠钱的是爷爷,借钱的倒是孙子了。”
骆玉珠呆呆地看着他:“可我怎么觉着咱两边都是孙子啊。”两人借着手电筒的光亮,照着一张张欠款白条不禁哀叹。在这深夜院门继续被人砸响着……
追债的人家里要不到钱,又到摊位上堵人来了。陈江河正往商城里走,一个商户逃难般跑来,不时地回头张望着。陈江河笑着招呼:“于叔,您这是干吗呢?鬼子追杀?您满脑肥肠的,看着也不像地下党呀!”商户忙冲他摆手,大光爹则上前引导:“先躲到仓库里去,走这条路!他们撤了我马上通知你!”
摊位前有一群人围着看热闹,一个女子打好地铺盖上被子躺在过道上。她发狠骂道:“姓于的!你躲得过初一,躲不过十五!不还钱我就睡在这!”大光爹冲陈江河摆手,示意他别管。陈江河皱眉打量周围摊铺,有的忙着收拾躲藏,有的正跟讨债的人拍桌子瞪眼。远远的,巧姑正笑脸应付着摊前坐着的几个人:“他们出去了,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……”陈江河警觉地停住脚步。巧姑一眼瞥见陈江河,连连向他暗使眼色。那几个人回头张望时,陈江河已经躲到了摊铺后。冯大姐笑眯眯地瞧着他:“江河啊,你顶天立地的个体劳协大会长,没想到你也躲哪?快!钻这桌子底下去,我今天已经掩护四拨人了!”陈江河尴尬地笑笑,恨不得抽自己的嘴巴。
眼看要过年了,催债的人越来越多,而那些欠陈江河钱款的代理商,却像从空气中消失了一样不见了,电话打去也没人接。陈江河思索:“看来不能坐在家里干等了,咱也得大过年地撕破脸皮堵人家门去了。”
骆玉珠说:“这就对了!你负责远的,我负责近的。”陈江河吓一跳:“你可别乱动!小心伤了胎气。”骆玉珠吐舌:“臣妾没那么娇气!大肚子还有大肚子的优势呢!”骆玉珠望着窗外,眼中满是杀气,一副要钱不要命、不成功就不回家的样子。
四
陈江河夫妇分头出门要债去了,王旭暂时借住到了巧姑家里。大肚子骆玉珠去的是一家杭州的公司,好不容易见到老总,老总也以资金紧张为由推脱,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。现在欠钱的是爹,骆玉珠进退两难,难道就这样空手而归?骆玉珠不甘心,她一咬牙:“我就坐在这里了,你不给钱我就不走了!”
骆玉珠平心静气地坐在走廊里低头织毛衣,过往的人都以为发生了什么桃色事件,躲得远远的。听说有个大肚子,整天坐在老公的办公室门前,老总媳妇赶过来,阴阳怪气地盯着织毛衣的骆玉珠:“死妖精,你这是干吗呢?”骆玉珠笑笑:“我等王总。”老总媳妇打量她,越看越像狐狸精,“等他干吗啊?”骆玉珠:“他欠我的,我要讨个说法。”骆玉珠又低头织起来。
老总媳妇妒火中烧,怒气冲冲找丈夫算账。一脚踹开总经理室大门,只听见屋里传出“啪!”的一个嘴巴声,“那孩子是谁的!”老总捂着脸:“我不知道!”媳妇怒道:“你不知道?她为什么会坐在门口讨要说法?”
“啪!骚公!”又一个嘴巴,“咱儿子才刚三岁啊,你就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了?”老总媳妇大声哭诉起来,骆玉珠像没听见一样,继续低头织着……
骆玉珠死死地盯着老总,老总跟人在饭馆吃饭时,骆玉珠挺着肚子坐在窗外织毛衣。老总只得尴尬地跟人解释……老总在街上走时,骆玉珠拎着毛衣跟上了,老总无奈地回头瞧着,骆玉珠停住脚步微笑着……老总不得不把骆玉珠请到办公室,“啪”的一声,扔出一捆钱来。老总哀求:“骆老板!你饶了我吧,我得罪不起,可是我确实只剩这些钱了!一共是两万,剩下的五万容我一些日子!”骆玉珠收起钱,将毛衣一递,笑脸相迎道:“兄弟,我这毛衣织小了,可是料子很好,送你家孩子吧!”
陈江河去长兴商贸城要债,代理商看到陈江河,愁眉苦脸地恳求:“陈老板,我是真的没有钱呀!我的货款也回笼不来啊!这些货您看中了哪些您就拿走吧。”
“你再想想办法,我要不是被人追得厉害,也不会到你这来。”代理商见到有顾客进来,便起身相迎,笑容可掬地将顾客引到屋里,送上茶水,完全忽视了陈江河的存在。
陈江河在商铺外面站了大半个小时,见代理商不搭理自己,起身想走,又停住脚步,咬牙回头望去,正好看见代理商匆匆出来。陈江河趁这个空隙走进商铺里屋。热水器的外封盖已经拆开,顾客正在犹豫着要不要进货,陈江河上前给客户拆装热水器,滔滔不绝地给顾客讲解热水器的构造特点,客户听得津津有味,继而频频点头。
“您看这热水器,它的隔温层是精心设计的,外行很难看出来。热水器档次差距就在这隔温层……”
顾客和陈江河一起走出门来,就像多年的朋友一样在门外分手告别,代理商从厕所回来,连忙上前阻止:“不好意思,他这个人不是……”顾客满脸不解:“你这位员工非常敬业,通晓热水器的构造原理,如果不是他讲解得清清楚楚,我还真有顾虑。我订五十台!今天能发货吗?”代理商不住擦汗,又喜出望外:“能,能发!我……”
陈江河给代理商促成了生意,代理商要请陈江河吃饭,两个啤酒瓶碰在一起,一沓散钱放到桌上,代理商钦佩地说:“讨债的我见多了,可还没见过你这样学雷锋讨债的!兄弟,你别嫌少,这一万先救救急!”陈江河感慨万千地仰起头,豪情满怀地举起啤酒干了杯。
五
陈金水坐在堂中扎鸡毛毽,巧姑带着王旭过来住几天。“把这野孩子带回家来干什么,你还嫌不够乱?”
巧姑不满:“爸!您小声点。”陈金水冷哼:“他们两口子逃到外面躲债,把孩子扔下不管了。这肯定是骆玉珠的主意。”巧姑急忙辩解说:“他们夫妻是出去讨债,不是躲债!”陈金水嘟囔:“你把他带回去睡他们自己家,别赖在我这,我看着就烦。”巧姑耍赖:“爸!反正我不管,我还有批货要包,你看着孩子啊!”陈金水忙抬头:“哎!怎么甩给我了?”
陈金水看到王旭正望着自己,甩手抛出一个鸡毛毽砸到门上,王旭一缩脖,鸡毛毽落在王旭脚下。王旭一蹦一跳地踢起,毽子在他脚上翻飞。陈金水诧异得很:“踢得不错啊。”
王旭蹲在门里:“跟我叔学的,他也会踢。”陈金水笑了笑:“他?你问问他小时候跟谁学的。”王旭钦佩地:“知道,跟您。”陈金水有些得意。王旭渴望地:“爷爷,您能教我扎毽子吗?”陈金水叹息道:“有什么用啊,这东西又轻贱又便宜,学它就学成废物啦。”
王旭认真地说:“可您说的鸡毛换糖就是这样,积少成多,一分钱能撑死人。”陈金水愣了愣,抬头打量起他来。王旭咧嘴快乐地说:“爷爷,是您在那婚礼上说的,我想拜师,想跟您学吆喝!”陈金水默默看着这个聪明灵光的孩子,眼神温润下来,喃喃地:“你这娃娃,聪明,机灵,乖巧!跟他小时候真像。可惜啊……”
讨债的厂商要不到钱急死了,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四处追着要。虽然已近黄昏,隔壁的很多摊点已经走人,但几个讨债的厂商还聚在陈江河的摊位前,争相拍桌子跟巧姑急:“陈江河什么时候回来?”
“骆玉珠欠我的首饰款已经三笔了,再过几天就过年了!”
“他们两口子不是跑路了吧!”
“刚才我去他家看了,院门紧锁,孩子都带走了!”巧姑忙着解释:“怎么会跑路呢,摊还在这。我鸡毛哥跟玉珠姐不是那样的人……”厂商不依不饶:“那咱就搬货,拿货抵债!”巧姑快哭出来,双手把住摊口:“不能搬!求求你们了……”
突然一棍子砸在台面上,所有人的手都缩回去。大光爹横着棍子一脸凶相:“干什么,你们,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,是吧?”
有人骂:“陈金土,你这个老油条,别老三老四装好人,你还欠我们的钱呢?”大光爹语气软下来:“又不是我一家欠,你看看那么多摊,谁收得上钱啊?全是白条!”
有人大声喊起:“还钱!不给钱,就在你们这过年!”巧姑被两个人拉扯着。大光爹怒吼道:“住手!谁再拉我儿媳妇,立刻把他的牙打下来!信不信?”众人松开巧姑退后,巧姑躲到大光爹身后,害怕地看着。
大光爹喘息:“不就是钱吗,老子要钱没有,要命有一条!”有人叫:“陈金土你要干什么?”大光爹摆手:“我还没说完呢,要牙有两颗!”大光爹背过身,用力一掰,两颗金牙拍在桌上,满嘴是血地扫视众人。巧姑含泪:“爸,爸您干吗呀!”大光爹含糊不清地:“金的,当年我儿子给我镶的,假了包换!”
人群鸦雀无声,身后响起陈金水从容的声音:“地主恶霸黄世仁啊!这金牙你们也好意思要,这可是人家吃饭的本钱哪!”众人回头看,陈金水拄着拐杖走来,仔细端详桌上的两颗金牙,又看看大光爹,扑哧一笑。
大光爹有点懵:“金水哥,你还笑?”
陈金水点头:“你平日带着这两颗破牙,臭烘烘地到处显摆,我都替你臊得慌,今个儿自己拔了,轻快多了吧?”
大光爹捂着嘴:“你就损吧!”陈金水转身扫视众人:“大过年的,干嘛都跟黄世仁一样,讨债的难,躲债的也难,都消消气。不嫌弃就住我家,饭管够,鸡蛋管够!”
巧姑吃惊:“爸?”陈金水笑着一挥手:“谁会下棋?把我哄高兴了还有鸡吃、有丹溪酒喝呢!”
六
骆玉珠要到了钱,心里不放心儿子。得知巧姑把王旭放在陈金水那里,急得快哭起来了:“你怎么把孩子跟你爸放一块呢!”
“没事啊玉珠姐!我爸又不是怪物。”骆玉珠把话咽回去:“你爸……”刚走到院外,听到里面王旭一声叫:“哎—”骆玉珠脸色一变:“坏了!”巧姑也是一愣,突然拉住骆玉珠。院里传来爷儿俩一唱一和的吆喝声。
“哎—鸡毛换糖咧—你得带着劲,让人听着嘴馋,再喊一次。”王旭喊道:“哎—鸡毛换糖咧—”骆玉珠不可思议地听着,巧姑也是目光惊诧。
爷儿俩的吆喝声越来越亮,响彻夜空。吆喝声中,响起一列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。
过年啦,家家户户办起了年货,可骆玉珠一点也感受不到年味,陈江河出门要债迟迟不归,最近几天更是一个电话也没有,骆玉珠不禁担心起来。看到人家都买新衣服新鞋子了,王旭特别羡慕,也问母亲:叔叔何时回家呀?骆玉珠寻思,在家等也是干着急,还不如带着儿子去看一下陈江河。
长兴街头,骆玉珠和王旭终于见到了自家那辆满是泥泞的货车。马路对面,陈江河正狼吞虎咽地吃着干粮,满嘴掉渣。陈江河胡子也没刮,狼狈不堪,噎得不行了,就凑到浇花园的水龙头前喝水去了。骆玉珠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,恨不得马上拉亲人回家。陈江河见到骆玉珠拉着王旭朝自己走来,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反复地揉着问道:“你们怎么来了?”
骆玉珠生气地说道:“你问谁呢?谁几天不给家里电话?”陈江河一抹嘴:“我不是怕你们着急么。我已经盯着老董好几天了,他走哪儿,我就跟到哪儿,我就不信邪,他敢不给钱?”
王旭几天不见,又长个头了。陈江河上前揉着王旭的头:“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?跟叔说说。”
王旭忙从书包里取出试卷,得意地递上。陈江河惊喜:“嚯!可以啊,90 分,在你们班排第几?”陈江河拉起王旭逗笑。
王旭伸出五个手指。陈江河乐:“第五?有出息啦!你妈没白疼你!”骆玉珠直勾勾地看着男人:“姓董的是个坏人,咱钱别要了。回家过年吧。”陈江河收住笑,转头看着骆玉珠:“回家怎么过年?我跑了这么多天才要来三万。家里多少人堵在门口呢。”夫妻俩无奈对望着。
老董西装革履地到酒店请客吃饭,客人来了不少,看来今天是个机会。陈江河与王旭爷儿俩坐在小货车驾驶室里,瞄着老董接来送往,客人进进出出的,丝毫不敢放松。
“小旭,你在这里别动啊!等你妈买饭回来。”王旭抱着书包点头。陈江河跳下车追到门口,一把拽住老董。老董回头哭笑不得:“怎么又是你啊!”
“老董,你有钱请人吃饭,没钱还我?你还一部分也行呀!”老董不耐烦地往前走:“陈江河我真服你了!请客吃饭是工作需要,懂吗?我也得打开市场,得赚钱!不然怎么还你?”陈江河追上几步:“老董,不能再拖了!你都欠几笔款了?”老董瞪眼吓唬道:“松开!你要是搅黄了我的事,跟你没完啊!”陈江河被甩到一边,眼睁睁看着老董追上众人,
陈江河懊恼地转身走出酒店,来到货车边,突然愣住了,他发现王旭不见了。
老董笑眯眯地招呼众人进入包厢:“昨晚打牌又赢了这么多,敞开吃啊各位……”老董拿出厚厚的一叠钱,夸自己命真好,一辈子有用不完的钱,炫耀后又塞回包里。王旭挤在人群中,一直紧盯着老董夹着的皮包,突然凑上前一抽,抢过就跑。老董惊呆了,大声叫嚷:“哎!站住!”王旭拼命地往楼梯间跑去。老董追出来,疯狂地喊道:“拦住他!拦住那小孩!”
陈江河正走进大堂左右张望,眼看几个保安正围堵包抄四处逃窜的王旭。王旭被一个保安拉住扑倒在地,皮包也摔出了老远。陈江河大吼一声:“住手!”另几个保安奔来:“这小偷还有帮手啊!”
陈江河扑上前抱住王旭,扫把棍子全都打在了陈江河的背上。王旭哭喊:“别打!别打我爸!”听到王旭喊的一声“爸”,陈江河竟忘记了背上的疼痛,呆呆地看着哭成泪人的王旭。
老董怕出事,连忙拦住几个保安:“别打了,我们认识!这是误会!”老董拉扯陈江河:“陈老板,你怎么让孩子抢我的钱呢!差点出大事了……”陈江河一把推开老董拉扯的手臂,眼睛不离抽泣的王旭,一堆散票拍到了手上。老董双手抱拳拱了拱:“我真服你了!就这点钱,带孩子吃点东西去!”陈江河像没听到一样,轻声问道:“小旭,你刚才叫我什么?”王旭抽泣着用手掩饰,递上捡起的票:“钱。”陈江河紧紧地将孩子搂住。
陈江河回到车上,骆玉珠正拿着保温盒等着开饭,见到爷俩青一块紫一块的,一脸诧异。王旭低声地:“刚才叔去要钱,被坏人打了。”陈江河急忙掩饰,扬了扬手中的钞票,憨笑着:“被打也值了,今天总算要到一点钱了。”
骆玉珠埋怨:“被打成这样,亏你还笑得出来!你不会踢死他几个!”陈江河得意地瞥了眼王旭,两眼放光:“我今天不还手,我高兴,玉珠你不知道,还有比要回钱更高兴的事呢,我听到小旭叫我爸了!”骆玉珠吃惊地打量着儿子:“小旭,真的吗?你叫他什么?再叫一声。”王旭不好意思了:“叔。”陈江河与骆玉珠无奈地交换了个眼神,却都露出了微笑。
小旅馆的窗外不时响起爆竹炸响夜空的声音。小吃店都关门了,一家人肚子饿得咕咕叫,终于王旭躺在骆玉珠的怀里昏昏睡去了。
陈江河端着一碗红豆糯米饭兴冲冲地推门进来。
“红豆糯米饭!小旭……”骆玉珠冲他嘘了一声,轻轻地把孩子放到床上,像变魔术一般拿出一包义亭红糖。陈江河轻手轻脚坐在地铺上,夹起一筷子喂到妻子嘴边。陈江河轻声问:“甜不?”骆玉珠笑着点头:“哪买的?”
“今天过小年,全都关门了,我跑了整个城找吃的,跑出很远才买到的。其实是别人家里讨来的,好人哪,他不要钱,我硬塞过去的。”陈江河再也不愿意去找吃的了,就拿出放在车上的粽子,昨天就已经发现粽子馊了,但为了填饱肚子,陈江河只好用开水洗洗吃了……
骆玉珠开心地笑着:“日子都过糊涂了,如果不听这鞭炮声,真忘了今天是小年。”陈江河长叹一声,轻抚孩子头发:“让你跟孩子受这么大罪,我真没有用。”骆玉珠坐在床沿,搂住地上盘坐的丈夫,下巴放在他的头顶:“比起我们孤儿寡母的时候,我已经很知足了,你我,小旭,还有肚子里的孩子,咱一家人能守在一起,在哪都是过年。”陈江河眼里闪着泪光:“当我今天听到小旭喊‘别打我爸!’那时候,我真感觉不到疼了。当时就觉着他能喊出这句,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。”
骆玉珠又夹起一筷子,自己吃一口,又喂丈夫一口,两人顶住额头相视而笑。窗外爆竹脆响,温暖的火光笼罩着小旅馆的简陋房间……
永康五金厂,夏厂长被讨要工资的工人堵在办公室里。要过年了,工人们的工资奖金却没有着落。
夏厂长心急如焚,又欲哭无泪:“我知道大伙要钱过年,我比你们还急!可你们逼死我也要不来一分钱啊!”一个工人质问:“咱们没停过一天工,效益那么好,怎么就发不出钱了?”夏厂长拉开抽屉举起一叠白条:“钱都在这呢,全是拖欠款,三角债!人家就是不给,我能有什么办法!”
夏厂长转身:“张会计?”会计直摇头:“厂长,我天天在催,没有一个人接电话。”夏厂长迟疑了一下:“陈江河也不接?”会计哭丧着脸摇摇头。众人对着夏厂长七嘴八舌:“厂长,月奖金、年终奖我们不要了,您就把工资发我们吧!”
“老婆孩子都等着过年呢,买肉的钱都没有哪。”
“厂长,几个月没发工资,我都不敢回家了,回去老婆都不给好脸色看!”“唉,这年怎么过啊!”夏厂长抱住脑袋蹲下:“我也没法过了,再给陈江河打电话,电话打不通,就打传呼机……”
七
北风那个吹,雪花那个飘。大年二十九,伴着歌声,陈江河一家三口兴奋地开车回家过年,身上的传呼机响起,陈江河停车,走进了路边的一个电话亭,回完电话,陈江河面色沉重地走出来,骆玉珠挺着肚子爬下车:“老夏又催了?”陈江河停住脚步:“老夏也没办法,厂里工人都跟他急了。今年不光是咱一家过不好年。”骆玉珠咬着嘴唇点点头。慢慢地,陈江河的眼光落在货车上,喃喃:“我有个想法,把车卖了,先救救急!”骆玉珠轻声说:“这车买来不到一年,才跑了几千公里啊,还是新的。”
自己再难过,年前也要让老夏把工人的工资发出去,那么多家庭啊!剩下的钱给其余几个厂家正好分了,咱家不把债留到明年。主意打定,为资金困扰多日的陈江河突然放松下来,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卸下了。
二手车市场里,已经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雪。骆玉珠搂住儿子,眼巴巴地望着丈夫陈江河跟人谈价。买车的人为难地:“非要现金?”陈江河斩钉截铁:“没现金我不会这么压价卖车。眼看就要过年了,我缺这钱。”买车的人迟疑地点了点头。陈江河笑了笑,将车钥匙递到那人手上。王旭突然挣脱开骆玉珠,扑到爱车前张开手臂,护住货车。“这车不卖!不许动我家车!”陈江河停住脚步,强笑说:“小旭,咱将来还会再买新的,买更好的车!”王旭摇头:“我不,我不!我还要坐着它上学呢!”骆玉珠忙上前搂住儿子,轻声说:“小旭,听话!”货车启动,陈江河转头眯眼看去,眼睛有些湿润。
雪花飘飘,寒风呼啸。夏厂长被工人困在办公室已经两天了。尽管催账的电话打了很多,可现在是非常时期,借钱的是大爷,要钱的是孙子,要钱等于割人家的肉,夏厂长已经收拾了干粮、被子和棉袄,准备在办公室过除夕了。
突然,窗外响起熟悉的喊声:“夏厂长,老夏!”夏厂长绝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恍惚着侧耳倾听,慢慢起身:“陈江河?”夏厂长推开众人来到窗前,陈江河风尘仆仆,头上散发着热气,抱着一个鼓鼓的黑包笑着。脸色雪白、小腹微隆的骆玉珠拉着儿子跟在后面,一家三口疲惫不堪地站在门外。夏厂长一脸不解:“大过年的,百多里路的,你拉着老婆孩子跑我们这里来干什么?”陈江河举起黑包:“货款!要不要?”
会计撒腿跑上前来接过,清点后喜出望外地举起黑包:“厂长!十几万哪!”屋里鸦雀无声,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欢呼声,大家争相涌进门去,将一家三口团团围住。陈江河被抬起,急忙叫道:“别抬我老婆,她怀孕了!”夏厂长怔怔地看着包里的一捆捆钱,望着被抛上半空的陈江河:“我的祖宗,你哪来那么多钱?”陈江河躺在半空大叫:“我们义乌有年前收账,安心过年的传统,永康应该也是这样吧,我把那货车卖了!”夏厂长哽咽:“兄弟,你这个新年礼包太重了,你……快给客人一家子准备吃的!”夏厂长没再说下去,泪水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不争气地淌落……

![【学习强国】[挑战答题]带选项完整题库(2020年4月20日更新)-武穆逸仙](https://www.iwmyx.cn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12/timg-300x200.jpg)


![【学习强国】[新闻采编学习(记者证)]带选项完整题库(2019年11月1日更新)-武穆逸仙](https://www.iwmyx.cn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12/77ed36f4b18679ce54d4cebda306117e-300x200.jpg)